科技与社会的共生

邱泽奇/文 当我拿到《共生:科技与社会驱动的数字化未来》这本书稿的时候,感到一阵欣喜。理由很简单,从腾讯提出将科技向善作为一种倡导开始,科技公司与社会对科技向善的理解与实践正在逐步迈向深入与务实,尤其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的 2020年之后。
科技公司是提供科技产品和服务的主体,愿意倾听社会的声音,是科技向善迈向务实的前提。与此同时,社会对科技产品与服务提供建设性的诉求,则是让科技迈向“向善”的有效保障。
冲击与反思
本书第 4 章收录了10篇来自社会各界的声音,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疫情冲击的基本判断。来自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朱恒源把企业、社会、技术放在疫情场景之下,指出尽管社会自身对科技的期待存在张力,但理解社会期待的复杂性依然是企业提供善的产品和服务的前提,理解人类适应能力的滞后性,其实需要整个产业界而不仅仅是科技界创新科技、企业、社会之间新的关系模式。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姜奇平提供了一个节奏性判断,指出疫情提供的极端环境改变了以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方式,出现了“线下主动找线上”的模式, 在产品与服务的关系中,把服务进一步推上前台,制造业的服务化迎来了一个转折点,从而把科技的社会价值推上了前台。
腾讯高级顾问、HR科技中心人力分析负责人廖卉从另一个视角指出,疫情的压力让“远程+现场”快速成为新的工作场景常态。与此同时,平台服务在劳动力市场的拓展让共享用工也提早到来,同时,对工作监管提出了新的需求。用人工智能监管劳动成为满足工作新常态的现实场景。进而,对人的人文关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人工智能的伦理议题就此进入了社会的现实,科技向善不再只是科技公司的社会价值倡导,而是开始进入社会生活。
第二类是对科技反应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指出,原本,判断是人的基本权利,可我们却把它交给了算法,疫情成了这一进程的推手。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常江也进一步指出,我们正在没有任何批判地拥抱科技带来的效率,却忽视了对技术的批判,进而直接丢弃了科技产品与服务中的人本精神。
科幻作家陈楸帆则忧虑,当我们把一切都包给机器时,人类还会剩下什么?当我们把教育当成纯粹的技术,而丢弃了对自我的寻找,教育便失去了其价值内核。正是在这个语境之下,曾毅尖锐地指出,当下,社会对创新的诉求极高,忽视了对科技伦理的关注,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发展亟须考量其对社会的长期影响,一方面要提升科技系统对社会的透明性,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跨部门、跨学科的协作,让社会的伦理倡导变成科技的伦理实践。
可如此,会引发科技公司竞争方向的调整,一如美国华盛顿大学福斯特商学院Philip Condit讲席教授陈晓萍所说,当科技的社会价值成为其产品和服务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企业的管理变革时机便已经出现,把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价值融入社会价值之中,将是管理革命的风口,也是竞争超越的契机。
伦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百岁人生》作者琳达·格拉顿则从技术进步和疫情冲击的双重视角探讨了教育、就业、医疗健康等领域的新变化,以及新兴技术所扮演的角色。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薛澜则跳出企业视角,站在社会一侧指出,企业是落实科技向善的主体,也是最有效率的主体,可规制依然是社会的、公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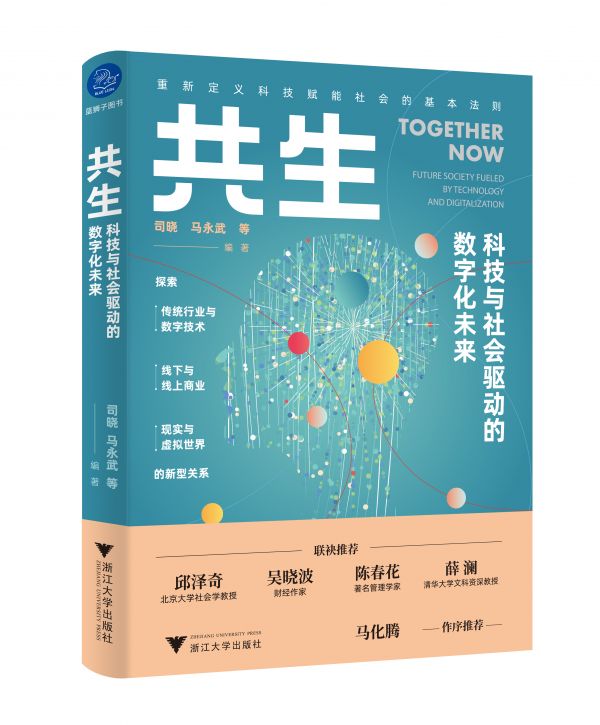
共生
作者: 司晓 / 马永武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科技与社会驱动的数字化未来
出版时间: 2021-8-1
共生是基本法则
我倒以为,科技创新的潮流势不可挡,历史如此,现实亦如此。其社会合法性,一如外卖场景被批判的算法,科技带来的是多方共赢逻辑的正反馈。批判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是必要的,却不一定是必需的。这是因为批判不足以解决科技的负面影响,只有建设才能最大限度地抑制科技的负面作用。
我还以为,数字科技的伦理建设的确到了转折点,可是,如果只是诉诸工业时代的伦理建设模式,不一定奏效。对企业的规制监管是必要的,却不一定非要站在企业的对立面进行监管。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讲,每一个科技创新与应用主体都可以被理解为数字时代的企业,把每一个社会行动者都作为其他行动者的对立面,会因对立而产生不必要的社会成本,显然不是优化且有效的监管逻辑,不是监管的初心,更不是监管的目的。
顺应数字社会的特征,把相关利益主体纳入其中,从工业化时代的控制性监管转向数字时代的服务性和协同性监管,似乎更有机会发挥监管的效用,更加适用于高度互联的数字化时代。在这个逻辑下,热议的透明性看似是顺理成章的监管原则,殊不知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难题。这是因为,即使把科技原理和算法代码置于透明环境,如果不能理解其中的原理与逻辑,依然无力监管,依然达不成监管目标。在科技创新有如星辰般浩瀚多样与复杂的环境中,回归人的社会性初心,或许是社会与科技让科技向善的同归之途。
作为回应和呼应,在新冠疫情的极端场景下,科技公司又如何能从社会价值出发,实践科技为人类服务的目标?我们看到了谷歌具有一般意义的模型卡探索,也看到了快手的流量普惠,B站对社区的再造,还有运用科技对自闭症进行干预。
更值得期待的是积极倡导科技向善的腾讯科技在疫情中的尝试与努力。 在人人禁足的环境下,线上是每个人真实与现实存在的空间,任何一条不经意的信息都可能有武器般的威力。其中,谣言成为干扰抗疫最重要的敌对力量。在抗疫过程中,削弱谣言的干扰性力量,是对抗疫最有力的保障。用数字技术辟谣,为科技向善做了最直接的诠释。
在对抗谣言的同时,如何快速、精准地识别感染者,除了医学方案,还有更加智慧的方案吗?人工智能给了人类一个新的选择,运用人工智能强大的学习与归纳能力,通过影像和声音识别无症状感染者成为阻断病毒隐性传播、赋能人类与病毒赛跑的新利器。禁足是有效的抗疫管理措施,也是传统措施,从传染性疾病给人类带来危害开始,人类就在采用禁足措施阻断疾病传染。在人类还处在相互隔离的时代,禁足不仅有效,而且对社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也相对有限。可在一个高度互联的时代,禁足,无论对经济还是对社会,其影响都是巨大的,人类理应借助科技的力量,寻找更加有效的防疫途径。用科技提升防疫的效率,在防疫环境中,用科技最大限度地释放人类的创造力,或许是当下对科技向善最直接的诠释。
2020 年,中国是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世界主要经济体,背后则是一系列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难题,譬如,如何既控制疾病的传播,又保障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有序开展?既为数字原住民赋权,又为数字移民赋能等等。这些问题,不只是政府面对的社会公平性问题,更是科技公司面对社会的产品和服务价值选择。科技公司运用数字技术为社会呈现了一份积极探索的答卷。
社会对善的诉求,无疑是理解科技带来社会后果的指引,积极的思考、忧郁的批判,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更加重要的是,在科技貌似越来越具有自主性的时代,科技实践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善意的倡导和批判,只有落实到为增进人类福祉的实践之中,科技向善才真正落到了实处。其中,科技与社会,缺一不可。共生,是运用科技增加社会福祉,用社会诉求推动科技创新的基本法则。
(本文摘自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邱泽奇为《共生:科技与社会驱动的数字化未来》所撰写的推荐序)
